本書是作者以一顆赤子之心, 體察天地山川��、人文世情所作的山水游記與人文訪記��。第一部分是隨心而發(fā)�����、隨性而作的寄情山水的游記 ; 第二部分是暢覽廟宇樓閣, 探訪人文古跡的訪記����。
1. 季羨林先生的游山玩水散文,既有中國傳統(tǒng)文人的山野情趣�����,亦體現(xiàn)著身為學(xué)者的季羨林的人間情懷���。
2. 季羨林先生的寫景散文�����,不拘泥于個人的喜樂哀愁��,俏皮靈動的文字背后�,體現(xiàn)著先生深厚的古典文學(xué)素養(yǎng)與俯仰天地之間的浩蕩之思。
3. 現(xiàn)代人久居都市牢籠�,季羨林先生帶著讀者一起賞味自然���,重返本真之樂�。
季羨林(1911.8.6—2009.7.11)�,中國著名文學(xué)家、語言學(xué)家����、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,翻譯家��,散文家�,精通12國語言。曾歷任中國科學(xué)院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部委員����、北京大學(xué)副校長、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�。
第一輯
寄意山水野情愜
002 / 黃昏
008 / 聽雨
012 / 聽雨
014 / 喜雨
019 / 登黃山記
040 / 登廬山
045 / 富春江邊 瑤琳仙境
052 / 富春江上
059 / 觀天池
066 / 換了人間——北戴河雜感
069 / 火焰山下
075 / 望雪山——游圖利凱爾
079 / 西樵山
083 / 西雙版納禮贊
089 / 游石鐘山記
092 / 游小三峽
099 / 飛越珠穆朗瑪峰
101 / 石林頌
第二輯
暢覽樓臺涌文思
108 / 登蓬萊閣
114 / 瓊樓玉宇,高處不勝寒
120 / 大覺寺
131 / 游唐大招提寺
137 / 觀秦兵馬俑
146 / 奇石館
151 / 在敦煌
171 / 中央電視臺南海影視城
179 / 德里風(fēng)光
183 / 逛鬼城
190 / 海德拉巴
198 / 漢城憶燕園
206 / 深圳掠影
210 / 星光的海洋
215 / 延吉風(fēng)情
220 / 春滿燕園
223 / 臺北街頭小景
226 / 重過仰光
231 / 別稻香樓——懷念小泓
黃昏是神秘的����,只要人們能多活下去一天,在這一天的末尾,他們便有個黃昏����。但是,年滾著年��,月滾著月�,他們活下去有數(shù)不清的天,也就有數(shù)不清的黃昏���。我要問:有幾個人感覺到這黃昏的存在呢�?
早晨�����,當殘夢從枕邊飛去的時候�����,他們醒轉(zhuǎn)來���,開始去走一天的路����。他們走著,走著�,走到正午,路陡然轉(zhuǎn)了下去�。仿佛只一溜,就溜到一天的末尾��,當他們看到遠處彌漫著白茫茫的煙���,樹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層金黃色,一群群的暮鴉馱著日色飛回來的時候����,仿佛有什么東西輕輕地壓在他們心頭。他們知道:夜來了�。他們渴望著靜息,渴望著夢的來臨�����。不久���,薄冥的夜色糊了他們的眼����,也糊了他們的心。他們在低隘的小屋里忙亂著�����,把黃昏關(guān)在門外���。倘若有人問���,你看到黃昏了沒有?黃昏真美呵�����,他們卻茫然了��。
他們怎能不茫然呢�����?當他們再從屋里探出頭來尋找黃昏的時候��,黃昏早隨了白茫茫的煙的消失�,樹梢上金黃色的消失,鴉背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���。只剩下朦朧的夜����。這黃昏,像一個春宵的輕夢��,不知在什么時候漫了來��,在他們心上一掠��,又不知在什么時候走了����。
黃昏走了��。走到哪里去了呢���?——不��,我先問:黃昏從哪里來的呢�����?這我說不清�����。又有誰說得清呢���?我不能夠抓住一把黃昏�����,問它到底����。從東方么��?東方是太陽出的地方�。從西方么?西方不正亮著紅霞嗎�����?從南方么�?南方只充滿了光和熱��?磥碇挥姓f從北方來的適宜了。倘若我們想了開去���,想到北方的極北端���,是北冰洋和北極����,我們可以在想象里描畫出:白茫茫的天地���,白茫茫的雪原和白茫茫的冰山��。再往北���,在白茫茫的天邊上,分不清哪是天�����,是地���,是冰,是雪�����,只是朦朧的一片灰白。朦朧灰白的黃昏不正應(yīng)當從這里蛻化出來嗎�?
然而,蛻化出來了�����,卻又擴散開去�。漫過了大平原,大草原����,留下了一層陰影;漫過了大森林����,留下了一片陰郁的黑暗;漫過了小溪�,把深灰的暮色溶入琤淙的水聲里,水面在闃靜里透著微明��;漫過了山頂�����,留給它們星的光和月的光�;漫過了小村����,留下了蒼茫的暮煙……給每個墻角扯下了一片�,給每個蜘蛛網(wǎng)網(wǎng)住了一把。以后�,又漫過了寂寞的沙漠,來到我們的國土里���。我能想象:倘若我迎著黃昏站在沙漠里���,我一定能看著黃昏從遼遠的天邊上跑了來,像——像什么呢���?是不是應(yīng)當像一陣灰蒙的白霧�����?或者像一片擴散的云影?跑了來����,仍然只是留下一片陰影,又跑了去���,來到我們的國土里����,隨了彌漫在遠處的白茫茫的煙,隨了樹梢上的淡淡的金黃色�,也隨了暮鴉背上的日色,輕輕地落在人們的心頭�,又被人們關(guān)在門外了。
但是�,在門外,它卻不管人們關(guān)心不關(guān)心�����,寂寞地��,冷落地���,替他們安排好了一個幻變的又充滿了詩意的童話般的世界���,朦朧,微明����,正像反射在鏡子里的影子�,它給一切東西涂上銀灰的夢的色彩�����。牛乳色的空氣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結(jié)起來�,但似乎又在軟軟地黏黏地濃濃地流動。它帶來了闃靜��,你聽:一切靜靜的���,像下著大雪的中夜�。但是死寂嗎���?卻并不��,再比現(xiàn)在沉默一點�,也會變成墳?zāi)拱愕乃兰���。仿佛一點也不多��,一點也不少���,幽美的輕適的闃靜軟軟地黏黏地濃濃地壓在人們的心頭����,灰的天空像一張薄幕���;樹木�����,房屋���,煙紋,云縷���,都像一張張的剪影���,靜靜地貼在這幕上。這里���,那里����,點綴著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。黃昏真像一首詩����,一支歌,一篇童話�;像一片月明樓上傳來的悠揚的笛聲,一聲繚繞在長空里亮唳的鶴鳴�;像陳了幾十年的紹酒;像一切美到說不出來的東西�。說不出來,只能去看�;看之不足,只能意會����;意會之不足,只能贊嘆������!欢鴧s終于給人們關(guān)在門外了���。
給人們關(guān)在門外,是我這樣說嗎�?我要小心�,因為所謂人們��,不是一切人們����,也絕不會是一切人們的�。我在童年的時候,就常常待在天井里等候黃昏的來臨�����。我這樣說�����,并不是想表明我比別人強����。意思很簡單,就是:別人不去���,也或者是不愿意去這樣做����,我(自然也還有別人)適逢其會地常常這樣做而已。常常在夏天里�����,我坐在很矮的小凳上�,看墻角里漸漸暗了起來,四周的白墻上也布上了一層淡淡的黑影����。在幽暗里,夜來香的花香一陣陣地沁入我的心里���。天空里飛著蝙蝠����。檐角上的蜘蛛網(wǎng)����,映著灰白的天空,在朦朧里����,還可以數(shù)出網(wǎng)上的線條和粘在上面的蚊子和蒼蠅的尸體。在不經(jīng)意的時候驀地再一抬頭���,暗灰的天空里已經(jīng)嵌上閃著眼的小星了��。在冬天�����,天井里滿鋪著白雪��。我蜷伏在屋里����。當我看到白的窗紙漸漸灰了起來��,爐子里在白天里看不出顏色來的火焰漸漸紅起來����,亮起來的時候,我也會知道:這是黃昏了���。我從風(fēng)門的縫里望出去:灰白的天空�����,灰白的蓋著雪的屋頂���。半彎慘淡的涼月印在天上�,雖然有點凄涼���,但仍然掩不了黃昏的美麗��。這時��,連常常坐在天井里等著它來臨的人也不得不蜷伏在屋里���,只剩了灰蒙的雪色伴了它在冷清的門外,這幻變的朦朧的世界造給誰看呢�����?黃昏不覺得寂寞嗎���?
但是寂寞也延長不了多久��。黃昏仍然要走的��。李商隱的詩說:“夕陽無限好��,只是近黃昏�������!痹娙瞬徽畤@黃昏的不能久留嗎?它也真的不能久留��,一瞬眼���,這黃昏��,像一個輕夢,只在人們心上一掠����,留下黑暗的夜,帶著它的寂寞走了����。
走了,真的走了����,F(xiàn)在再讓我問:黃昏走到哪里去了呢�����?這我不比知道它從哪里來的更清楚�。我也不能抓住黃昏的尾巴,問它到底��。但是�����,推想起來�,從北方來的應(yīng)該到南方去的吧。誰說不是到南方去的呢���?我看到它怎樣走的了���。——漫過了南墻�;漫過了南邊那座小山,那片樹林���;漫過了美麗的南國�����。一直到遼闊的非洲��。非洲有聳峭的峻嶺�,嶺上有深邃的永古蒼暗的大森林。再想下去��,森林里有老虎——老虎�?黃昏來了,在白天里只呈露著淡綠的暗光的眼睛該亮起來了吧�����。像不像兩盞燈呢�?森林里還該有莽蒼葳蕤的野草,比人高�����。草里有獅子����,有大蚊子���,有大蜘蛛����,也該有蝙蝠,比平常的蝙蝠大�����。夕陽的余暉從樹葉的稀薄處�,透過了架在樹枝上的蜘蛛網(wǎng),漏了進來�����,一條條燦爛的金光���,照耀得全林子里都發(fā)著棕紅色�,合了草底下毒蛇吐出來的毒氣����,幻成五色絢爛的彩霧。也該有螢火蟲吧�����,現(xiàn)在一閃一閃地亮起來了���。也該有花�����,但似乎不應(yīng)該是夜來香或晚香玉�����。是什么呢��?是一切毒艷的惡之花�。在毒氣里,不正應(yīng)該產(chǎn)生惡之花嗎����?這花的香慢慢溶入棕紅色的空氣里,溶入絢爛的彩霧里�����。攪亂成一團���,滾成一團暖烘烘的熱氣。然而�,不久這熱氣就給微明的夜色消溶了,只剩一閃一閃的螢火蟲,現(xiàn)在漸漸地更亮了�。老虎的眼睛更像兩盞燈了,在靜默里瞅著暗灰的天空里才露面的星星����。
然而,在這里���,黃昏仍然要走的���。再走到哪里去呢?這卻真的沒人知道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!S了淡白的稀疏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的天空里去嗎��?隨了眨著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嗎��?壓在蝙蝠的翅膀上鉆進了屋檐嗎���?隨了西天的暈紅消溶在遠山的后面嗎����?這又有誰能明白地知道呢?我們知道的���,只是:它走了���,帶了它的寂寞和美麗走了,像一絲微飔�����,像一個春宵的輕夢����。
是了����!F(xiàn)在�����,現(xiàn)在我再有什么可問呢�����?等候明天嗎���?明天來了,又明天�����,又明天��,當人們看到遠處彌漫著白茫茫的煙�����,樹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層金黃色����,一群群的暮鴉馱著日色飛回來的時候,又仿佛有什么東西壓在他們的心頭�,他們又渴望著夢的來臨。把門關(guān)上了�����。關(guān)在門外的仍然是黃昏����,當他們再伸頭出來找的時候���,黃昏早已走了。從北冰洋跑了來����,一過路,到非洲森林里去了�����。再到���,再到哪里�����,誰知道呢��?然而���,夜來了,漫長的漆黑的夜,閃著星光和月光的夜���,浮動著暗香的夜……只是夜�����,長長的夜,夜永遠也不完�,黃昏呢?——黃昏永遠不存在在人們的心里的���。只一掠��,走了�����,像一個春宵的輕夢��。
1934年1月4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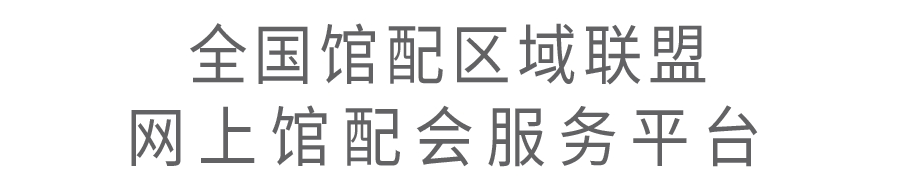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