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是當代文壇著名作家荊永鳴老師中短篇小說的一部精選集����。荊永鳴在中短篇小說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,而且以貼近生活的風格——既有對家鄉(xiāng)的懷念��,也有對北京的的依戀�����,深受讀者喜愛�。這部小說集則集中了作家中短篇小說的精華��。
荊永鳴(1958—2019)���,內蒙古赤峰市元寶山人��。著有散文集并發(fā)表中��、短篇小說多篇���。作品曾獲全國煤礦文學創(chuàng)作“烏金獎”����,內蒙古自治區(qū)文學創(chuàng)作“索龍嘎”獎����。短篇小說《外地人》獲“新世紀第一屆北京文學獎”、《小說選刊》獎���,中篇小說《北京候鳥》獲《人民文學獎》����。并有部分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連續(xù)劇���。系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會員����、魯迅文學院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員����。曾在平煤(集團)公司駐北京聯(lián)絡處工作,2019年4月11日在四川宜賓逝世����,
目錄
外地人
口音
北京候鳥
白水羊頭葫蘆絲
創(chuàng)可貼
大聲呼吸
坐席
北京房東
北京鄰居
較量
出京記
附錄 荊永鳴小說創(chuàng)作年表
不退���。
……不退就不退吧。
那就走吧���,上車�。
車子是輛破夏利�����,開得嗡嗡響�,好歹沒在路上散了架。到了地方一看�����,房子沒說的��,位置��、設施都挺好�。一問租金����,眼球卻差點蹦出來��,這不是在訛人嗎�����?話一出口����,房主的眉毛都立起來了�����,師傅�����,您怎么說話呢���?想租就租����,不租拉倒�����,什么叫訛人啊,是不是����?遇上這樣的茬兒,你不生氣就怪了��。心里想����,快去個屁的吧,我不租了可行吧�����?于此之下�����,那二百塊錢的“勞務費”就這么打了水漂兒——我剛到北京尋找開餐館的房子時����,就經歷過這樣的事情��。兩次之后才恍然悟出這是個騙局,是個圈套�!當然了,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圈套����,鉆不鉆,全憑你的智慧��,同時也在于吃一塹長一智�。比如這一次租房,我就沒去鉆那種騙子公司的圈套�����。
我鉆的是胡同�����。
北京的胡同太多了——猶如這個城市肌體中的毛細血管�����,不計其數(shù)�����。當時,我鉆的都是我餐館附近的胡同:大紗帽胡同����、南口袋胡同、磁器胡同����、取燈胡同……尋尋覓覓,一連轉了好幾天���,沒找到一家出租的房子��,倒是遇見不少戴著“治安”袖標的老頭老太太����,他們一律用警惕的目光看著我��。每當這時���,我就趕緊迎過去�,弓著身子�,討好地叫著大爺大媽,問附近有沒有出租房子的。
客氣的���,說沒聽說。
冷漠的���,說不知道����。
熱情的��,說想租房啊�,您得去找中介公司,知道嗎�?
白扯。一點用都沒有���。
后來我才知道����,想出租房子的人不是沒有�,而是有關部門管得太嚴,房子不能任意出租——尤其不能出租給不托底的人����、不明身份的人���、不三不四的人,更甭說���,萬一鬧出個販毒吸毒�、賣淫嫖娼�、殺人越貨等刑事案件來,房主要負連帶責任�����,輕者罰款��,嚴重的���,沒收房子的都有�����。因此一向遵紀守法����、謹小慎微的北京市民,即使有房空著�,鎖著,哪怕讓蜘蛛在各個角落里忙忙碌碌地結網�,也不敢輕易租人,更不敢到大街小巷去張貼小廣告�。不像后來����,小廣告到處都是,害得那些城管人員怨聲載道���,整天捏著那種塑料的大可樂瓶子往上滋水��,洇��,然后用小鏟子或小刀片之類的工具�,細著眼睛一張張地清除��。好不容易清理出個模樣了�����,差不多了���,本以為明天掃掃尾��,就徹底OK了�,可第二天一看,又是一層��!氣死�����。
我租房的時候����,北京的大街上還沒有那么多的“牛皮癬”,胡同里更少���。偶爾發(fā)現(xiàn)電線桿或廁所的墻壁上貼著巴掌大一張小紙���,我都會眼睛一亮,湊到近前一看��,卻是“包治各種性病��、尖銳濕疣����,一針就好”��。
我沮喪�����,妻子也如此�。她說北京怎么這樣呢��,有錢都花不出去���。我說還是錢少,有個百八十萬的試試��,賣樓的多得是���,打個電話說不定就會有專車來接你�����。結果竟把我妻子說惱了��,她說你想租就租�����,不租拉倒�,少跟我抬杠行不行?其實我說的都是實情����。后來,就在我們一籌莫展的時候��,倒是胡冬給我提供了一個信息�。
他說,大哥�,聽說你想租個房子?
我說����,找了好幾天了,沒有����。
他說,嗨�,你咋不早說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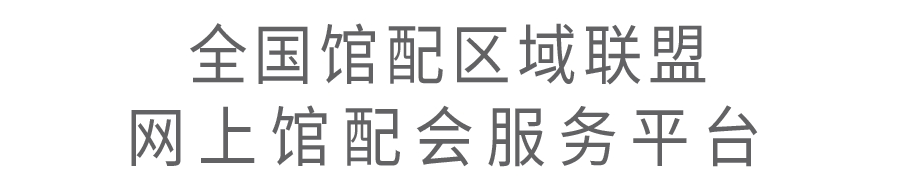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