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與攝影:我的一種存在與言說方式(代序)
每次旅游��,我都沒有文字留下�����,我從不寫游記����。最初以為是自己文字功力不足,但細(xì)想起來(lái)���,這只是一個(gè)表面的原因���。更深層次的問題是,自然���,包括自然風(fēng)景�,恐怕不是語(yǔ)言文字所能描述的。語(yǔ)言文字只是人的思維和表達(dá)的工具�����,在自然面前��,就顯得無(wú)能為力��。
坦白地說�,面對(duì)大自然,我常有人的自卑感��。那些大自然的奇觀�����,使你感到心靈的震撼����,而無(wú)以言說��。
正是這一點(diǎn)�,顯示了攝影(包括電影攝影)的力量和作用。所謂攝影,本質(zhì)上是人和自然發(fā)生心靈感應(yīng)的那瞬間的一個(gè)定格���,是我經(jīng)常喜歡說的瞬間永恒���。它所表達(dá)的是一種直覺的、本能的感應(yīng)(因此我堅(jiān)持用傻瓜機(jī)照相��,而反對(duì)攝影技術(shù)的介入)��,不僅有極強(qiáng)的直觀性���,也就保留了原生態(tài)的豐富性和難以言說性���。這正是語(yǔ)言文字所達(dá)不到的。攝影所傳達(dá)的是人與自然的一種緣分����;攝影者經(jīng)常為抓不住稍縱即逝的瞬間而感到遺憾。這實(shí)際上意味著失去了�,或本來(lái)就沒有緣分。
于是����,我的自我表達(dá)�,也就有了這樣的分工:用文字寫出來(lái)的文章����、著作,表達(dá)的是我與社會(huì)���、人生�,與人的關(guān)系��;而自我與自然的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�,則用攝影作品來(lái)表達(dá)���。
我經(jīng)常在學(xué)生與友人中強(qiáng)調(diào)攝影作品在我的創(chuàng)作中的重要性�,甚至說我的攝影作品勝過我的學(xué)術(shù)著作的價(jià)值��。這其實(shí)并非完全是戲言���。對(duì)于我來(lái)說,與自然的關(guān)系是更重要的:我本性上是更親近大自然的�。只有在大自然中�����,我才感到自由����、自在和自適�,而處在人群中,則經(jīng)常有格格不入之感�����,越到老年越是如此��。
即使是旅游�����,我對(duì)所謂人文景觀始終沒有興趣�,我覺得其中虛假的成分太多。
真正讓我動(dòng)心的��,永遠(yuǎn)是那本真的大自然�。這樣的類似自然崇拜的心理,還有相關(guān)的小兒崇拜���,其實(shí)都是來(lái)自五四我承認(rèn)�,自己本質(zhì)上是五四之子。
(摘自《旅加日記》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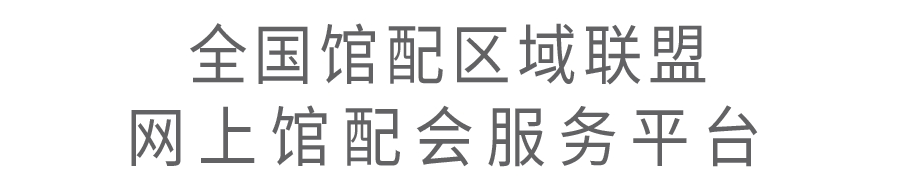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